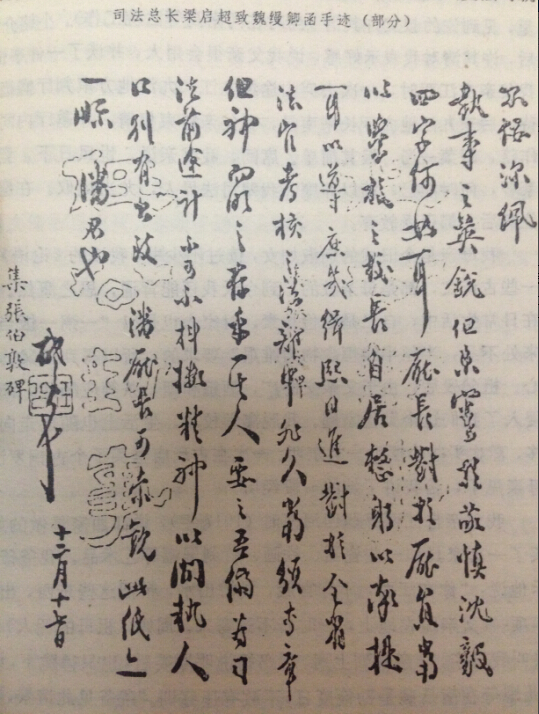κ���䡢���ʱ�ں��ϸߵȼ������쳤
|
κ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ϸߵȼ������쳤κ���䣨κ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ϡ����ܵ�42����-1992���2�� ���ߣ�κ���� �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䣬κ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ڴ壨���Ͻ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ɴ�ѧ�ñ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繤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֪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Ĺ㡣֪��֮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ϧ����ɾ͡�����Ϊ�˸���־���α����׳��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֪�ȸ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ڿ����κ��ϸߵȼ������쳤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ҵı�ķ���ֱ��30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ҵĵ�һ��Ů���ı�ķ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⸸���幫������ȥ�ġ����Ҵ�Ů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�ĸ���ҳ�һ��С�ٳ���˵����үү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Ҹ��뿪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¡� ��ʱ��1912--1913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ͬ�پ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˺ܶ࣬ʡ�Dz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dz����С���ʱ�Ҽ�ס�ڿ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Žֱ�ͷ·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ĸ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Ϸ�Ժ����ס�£�˵�����ò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絾���ѧ��ҵ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ͬѧ��ס�����죬�Ҹ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˵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Ҹ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ŭ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㣿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ҷ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û��ƾ�ݣ�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ڴƻƣ��㶼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蹫�ã��Ҳ��ˣ����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ɱ�ˣ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û�취�ң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֪���Һ��㸸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飿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ĸ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㲻Ӧ�úͶ��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𣿡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׳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䷨ʱ�ͺ��Ҹ���ʶ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ײ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ʱ��ĸ�ײ�Ը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游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ھ������游ͬ�ٷ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Ҿ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 1930��ǰ�����ڼ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ֵ�ͬ��ͬѧ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常�����壨��ʱ�ں��ϸߵȷ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ʾ�øУ�˵�Ҹ��ܻ����ˣ���̸��һ�����顣�Ҹ����ڽ���ʱ��һ��ȥ®ɽ;���Ž����Ž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ʢ�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㣬�IJ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ϯ�䣬�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к��ݣ���ʱ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˾�����ˣ��ȵ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ĸ���Ǹ���ʽ����績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Ҷ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ʫ�ģ�����ĸ�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ܱ��У�˼֮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Լ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أ��Լ���Ҳ���ԡ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˿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衱Ҫ��ġ����Եõ��游�Ļ��ġ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ι���ۺ��̡����Ӧ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֮�����ݳޣ�ϲ����ЩС����һ�ණ����һ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ͭ����ĸ���ˣ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ξ�����
�Ҹ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ְ�غ���ʱ(1917�꣩��˵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ĺã�����һ�Ҿߺ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̌η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үү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룿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ϣ�һʱ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裨��ĸ��Ӷ�ˣ���ȥ����ĸ�ף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ԭί��Ҳֻ�ù��£�˵�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�ϲ�ȷ���ڼ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Υͥѵ����үү�����龰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ڼҶ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Դ�Ҳȷʵ��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ڼ�ͣ�˼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ල���Ź㽨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ǰ�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Ǽҹ�ȥ���Ų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үү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δ�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ү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ʱ��·Զ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ɡ����Ҹ��ʹ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Ƹ�(���ǹ�ȥ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Ƹ����ҵĹñ��֣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ĸ��ȥ��
�º���˵�Ҹ����Ǵ�ȥ���ݣ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Ҫ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ݺ�ȥ�ػ�һ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Щ�ƴ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ͭ����ȣ��游���û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Ƹ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У���Ҷ����˲��ٿ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ư�·˽���ܻ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Ҹ�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Ź㽨�ڶ���ί�Բ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ദһ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ͣ����жػ�֮�С��Ź㽨���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׳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ί�Ա̿����վֳ�����˵�˾�һ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𣬶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ξ��꣬���ഢ���ȥ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˷��ƵĻ��ᣬ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©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Ǯ�ģ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а��²�˰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˵��ʱ���ʱ��¶�ġ�
�Ժ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ְʱ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̻�֣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־��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Ҹ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Ů���Ŷ����ĺ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ڴ��ż��Ϲۿ��ֵ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ǰ�棬��Ů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Ǯ���δ����ۻ��ˡ��ڱ̿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ͬ�磬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ǿ�ȥ���Ӳӵ�С���Σ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۵�ͭ��Ʒ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;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ز�Ʒ����غ컨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ëƤ�ȡ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·�ϱ��ĸ���Ҫ�Ȼ����غü������ڴ�ɭ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ˣ���ߵ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DZߵ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ý�һ�ž����ˣ���֪���굹�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ҹ��ʱ����˯������Χ�ɵ�ȦȦ���棬�Է�Ұ���ߡ���ɰ��Ķ����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˿��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Լ��糤��ɷ�Ǻ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˿��Ҫ�ÿ��öࡣ���˵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�˿��װ�ţ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˼��ˣ�˵���ֵǮ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ë��Լ�����糤����Ӳ�ú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С��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
��Լ��1920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£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ǡ���ʱ�游�챱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վ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֮��ĸ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Ų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Լ��1922�괺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Ҽң�֣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游��ס��ȥ�� ��ʱ��ֻͨ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һ�κ�·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ӭ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絽�ĸ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ɻ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ĸ���ס�˼��죬�����游�ӵ����ݻ�ݣ���Ҳ��ȥ�ˡ����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м�ɽ��ˮ�أ��ܶ��˺��游��ˮ���м�ļ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첻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Ҽǵ��β�³���游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䷨���¡���Щ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ʱ�游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100Ԫ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ĸ���ס��Щ�죬��ĸ�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游ס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ԭ��ʮʦ�Ų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ʱ�常����ĸҲ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ڼ��游����д�֣��Ѳõ��ķ���ֽ����д���ָ��ң�����ȫ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ĸ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ڻ��ز���ʱ�䣬��Ȼ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û��פ�������Ļ̡̻���ʱפμ�ϵ����Ծ��ڱ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Ԣ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أ��븸��ȫ��ȥμ���ݱܣ�ȫ�Ҷ�ûȥ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ճǼ���Χ�������常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ҹ�ڳ���Ѳ�أ��常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װ칫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שǽΧ�Ÿ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Χ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ƽ̹�ݵأ��м��и�ש̨��վ��̨�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ȫ�ǵĸ߸����常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常�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罻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֪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ȫ�Ҽ�����ש̨���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һ���常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dz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ɻ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£��˺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δ�Լ��Χ�ǵĵ����죬�常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ˣ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Կ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Ԯ���Ѵ��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Ԯ�����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磬˵��С����˲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ȥ�˵ġ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ˣ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ȥ���ˣ��µļ���˯���ţ����۾Ϳ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λ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Ц�Ŷ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Ź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ǵľ�����һ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Ű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��ķ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˸����棬��˼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Ӳ��ʡ��ط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ױ�ʾ���⡣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ɡ��һ����ɡ��Χ���´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糤����ָ���ĺ졢��ɫ�д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ڹ��类������֤չ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ɡ�ã��游����ĸ���常��ͬ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ƽ½���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飬δ��ǰ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ʮ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ң�ޣ��ǹܲ�¯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С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˵ǰ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ã���ȥ���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費�ҳ����Ժ�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͵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ò����磬�ƻ�ͨ������ľդ�Ѵ������߸�����դ�⼷�˺ܶ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ա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ǰ�棬��ľդվ�š������м��ǿյأ���ľդ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һ�߶�ߵ�̨�ӣ��ϱ߷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Ͳ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Ŵ�ӣ����ֺ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߿����˺��ྲ��һ�����졣ң��˵���Ǻ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ɾ����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͵ķ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У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ԩ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һλ��̫̫��һ�����ϸ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ұߡ���̫̫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ӱ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𣿡����ϸ�Ů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ˣ��Ҿ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ʱ�Ҿ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ô�ῴ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˹�����̫̫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µġ�����Щ��˵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ˣ�˵�Ķ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˻���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а���Щ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ñ��Ӵ�ң��˵�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߰ɣ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ǡ�ɱ�����Ӷ�˿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Ҳ����㣬���ȥ�ɣ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ĸ��ɶҲû˵�����ҹ��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ɣ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ĸ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ã��غ��Ͼ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˵�����ͺ��ʰ������峯��ࡣ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쿪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ʦү������Ӣε������ͬ�磩�˺ã���˵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ү��һ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һ�䵥�䣬����˰ѵ�������䷿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ڵ��¿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ˡ�����ǰ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ŷ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ݵ�һ�ߣ���ũ��ι���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ɸ��ӣ����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ľ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ܷ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˰ѵ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˵�ͷ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3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ϣ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ŵ���ʲô�ˣ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˵�Ǹ�̰�۵�˰�٣��ɱ��ԭ����Ѻ�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룺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裬�ٲ��˰���˭֪���ݺ�ĸ��Ц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ɣ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Ҹ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ʦү�ʹ����ײŴ���ȥ���ġ�
��Լ1923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´�ת���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ڻ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ڻƺ��к�����Զ��һ�Ρ�����ׯλ�ڻƺ�é��ɿ���Լ20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У���һ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أ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Ǩȥ�ģ������˳�֮ΪС��ˮ�����ɽׯס�м�ʮ���˼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ķ��ӣ��ȿ���Ҳ�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Ǿ�ϸ���οջ��ܣ��׳ơ�ɽ���ķ��Ӻá����ŷ��鴫���游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飬ǽ�Ϲ��˼����Ѻ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ı������β�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ˮ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ĸ����ʱ��Χ�����游ĸ����Χ���游˵�����ⲻ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常��Ц�ˡ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ŵ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Լ300�ף�����һ��Լ500���ĺӡ��Ӷ���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ǹŴ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ϴ���ӡ�˳������Լ20���ǻ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ȥ��˵Ұ���ںӱߺ�ˮ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µ�һĶ��յأ�ԭ�����Ƿ��ӣ��常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Ͷ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߲ˡ�ĸ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һ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ǧ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緹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ʱ�ͷ����游��ʱҲ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ʱ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ƣ��滨ĩ��ͩ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׳�����ȥϴ���ӱ�ϴ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Ĺ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Ŵ�Ԣ�Եȡ�һ�죬�ƺӷ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ȥ����ͬȥ����ʮ���ˣ�˳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ţ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ˮ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ͷ�Σ����ŵ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˵:����ƽ�ȣ�ȴ�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о���ȥ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Щ��ȴ�µ�ˮ���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㿴�����ǵı�����¸ң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˵�Ǵ�����ˮʱ��ģ��Ҳ��ţ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˴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Ĺ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Ҫ�¸ң�Ҫ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ʹ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и����˽̵���
1924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磬�ұ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游���ڲ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ײ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ʯͷ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常���游���ؼ�ȥ���游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һ��ҩ�������ٳԣ�˯��һ�졣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κ����ģ���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үүϲ���㣬��Ҫ�뿪�����ҿ��游��û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˶��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游�����ҵ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س����ˡ��游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绹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ィ��һ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ˮ���е�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¼���
��ȫ�ҷ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ƣ�ס��֣�ݡ�1928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þӱ�ƽ�ĺ���ͬ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ֻᣬ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Ϊ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ԥ��ר�����ذݷá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Ž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⣬���̶���ԥ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Ҹ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־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ʡ���ֻᲹ��һ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¥���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ݣ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Ԫ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ϸ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Ҷ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۱���ˣ���ͬ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Ҷ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۱���ˣ���ͬ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Ჿ�����ȥ��ǰ��ɳ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ӳ����д�վ��֣��վʵ�����Ҹ�һ�˸���֣���Ǻ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Ŧ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Ҹ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ṹ�������䵱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ҩ�Pο��Ʒ�����泵�����д�ӭ�͵ȣ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ʱʢ�ÿ��Я��ҩ�Pο��Ʒ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ļ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Ӳ���վ�ϳԷ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վ�Ϲ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ҾͲͣ���룬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롣����һ��֣�ݻ�վ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ҼҸ�֪���ƺӱ��ǣ����ܹ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Ҹ���ҹ��վ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Ϲ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Żء�1947�꣬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ף�˵��ȫ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Ǵβ��й��ӵ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ʱκվ��ָ�ӻ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Я�ף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ˮʪ�ˣ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һ·�ϼ�ʮ���д�վ��ֻ��κ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˵��ԥ���˻����Ľ϶࣬ԥ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س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£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á�
֣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Ժλ��֣�ݺӶ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Ժ����Ժ��1927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飬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֣�ļ���ʽ���ͬ���Է����˽��ġ���ʱ�Ҹ��װ��Ҽ��ڴ�ͬ·���з��ۼ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ƶ���ͯԼ�����ˣ�ѧϰ�Ļ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Ļ�ѧ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ź�һλԬ��Ů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б�֯������ϯ������飩��֯ë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Ƹ�뼼ʦ���ڼ��ա��Ҹ����Ƕ��³�����һ��Ժ���ǻ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洺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ɳ�Т����۱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˹ܲ�Ʒ���շ����ɹ���ҵ��ְԱн����30Ԫ����ʦ���ʽϸ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ƽ�⡣1932����Ҹ��뿪֣�ݣ�ĸ��Я���˸���ƽ��ס���ҶԽ���Ժ�Ժ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˽��ˡ�ֻ֪���̻��Է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ˣ����ι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ƺ��ˣ����κ���ʡ��Ա����1935���Ҹ��ײ��ʺ�����֣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常ͬ��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֣�ݼ�³��ˮ����˾��ˮ����˾�аٻ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ɹ���20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1Ķˮ��3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ɲ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ׯ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ɸ��ذ���Ķ����һ�ʿɹ۵IJ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Ӻ��˷ܣ����ﻮ������չˮ������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.�ߡ��±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ίԱ��ӹܡ���սʤ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ܡ�
֣��ƶ��ҽԺλ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ʱ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Ժ---����ҽԺ�ͻ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ǽ̻��ģ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ʽ�һЩ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豸��ª�����㲻�˴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ʱ�и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ͥ��ҽ�ƴ�ѧ��ҵ�����ٴ����飬�ڸ��ٽֿ���ͥ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ʱǨ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̸��֣�ݵ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˵��뷨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һ��רԱ�Ϲ��콨����ƶ��ҽԺ����ר���ṩ���ֹ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̽�ļ��һ���֡�ƶ��ҽԺ��1932�꿪ҵ�����β���֣��ĥ�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ͤ��֣�ݶ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֣����ѻ�´��ˣ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λ�ơ���ҽԺ�豸��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ҩ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ڻ�ӭ��1933��ƶ��ҽԺ��Ϊ֣������ҽԺ��
�Ҹ��Դ����游�⣬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ҵ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Ϊ���ɿ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ܴ�һ��Сѧ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蹵���ű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йأ��ȳ�¼�ں���Ⱥ��ռá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ż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蹵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ԣ�ͬ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ά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佧���ߣ����м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ʮһ�꣬�巨����ةκ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־ 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δ�꣬�����ȼ�ˮ�ֻ����ӹ�רԱ��ԥ�칫�⣬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᳤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ǧ�ٰ߰�ʮ�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һ����ʮһԪ�����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ۺ���һ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֣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֮�ȣ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¡��ϲţ����߽��ģ���ռ��裬���ƽ��£�����Ϊģ����ʯ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һ��һ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ɶ��ߡ�����ģ�ɣ�ģ�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ģ���űӣ��Ź̶��ް�ʴ��Ҳ��ൺ�����ǵ��Ϊ̹;���õ�ʱ��ú�����κ��ة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Ȼ֮�գ����вŽ������ߡ�
ԭ����: ���ߣ�κ���� �Ͻ�Ե��
|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Copyright © 2001-2021, Tencent Cloud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