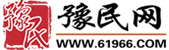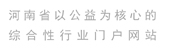���
|
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Ȼ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ǰ����;��δ�ƶ����Ʊ�Ҫ˫��ȥ��·̽Ѱ�� �Ҳ�֪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ů���ޱ�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Ĭ�û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۹⿴����ģ�ֻ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ؿ����ⰹ��Ļ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ɿ�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ʹ��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Ҳ�ɰ�Ϣ���ߡ��˹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ɶ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 ����ָ�µ��̞¾����Ե���㣬��ٿȻ�����м�ֻ֩����ҵ���ǰ�ϴ�˿���¡�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Ρ�һ��տ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ܰܰף����ּŵ�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׳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֩����һ���ĵĸֽ�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 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࣬���ܻ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ѪҺԴ�����ġ� �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ȿյľ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ȥ��ȴײ̱��ǽ�ǵľ�ƿ�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ֹ��ڳ��õ�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Լž����Ҷ�Ȼ�о�����¿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ֻ��Ƶķ��̣��Ҿ��˷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�ϵ�ѥ�Ӱ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ķ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Ĵ��̣�ʹ�Ҳ��ð�Ϣ����֪���ִӺδ��ܳ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ߴߴ���Ŵ��ҵĽ����ܵ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£�Ȼ���¸ҿ���һ�ۣ���ʤ�Ƶ��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֪��Ҫ��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ֻ����Ϩ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ܲ�ȥ�뵽è���һ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֮���ұ㼱����Ҫ��Ϊè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էȻ���룬�ɲ��˳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Ȼ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䰮������è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ѩ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¿�һ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÷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÷�İ飬���÷����ˣ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��õİ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̶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Ĺҹ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ɻ��ñ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ã�Ҳ����Ƭ��ʱ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ܾ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Ƿ��̫�ã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鶼���Ĺ�еļ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õ�ɻ��ñ��ȴ��ʼ���˹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��ӵ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η���ȴ�ܸе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һ��Ĺ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ȷ����ֻèһֱ�ڸ����ҡ� 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ǽ��ճ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è�Ĵ��ڡ�Ӧ�þ�����ֻè���Ҹ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è�� ��ë�ܰף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顣���鰲���ķ��ڵ��ϣ�ǰצƽ���ţ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ǰצ�ϣ���һ����˼ڤ��ĺ�ͯ����ͯ��Ĭ�ţ�����ij�Ĭ�ţ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ƽ�ĵ��档 ��ſ���ſ�ʱ���ұ�ע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Ҳ�֪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��춯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צ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İ��࣬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ߣ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ʵҲֻ����ƭ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۾��վ��ܶ��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µ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Ϊʲôһ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Ŀ�ġ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ŷ�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è����Ϊ�ĺ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α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롣 �ǵģ�����αװ����Ȼ�Ҵ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ݿ�ʼ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Ĺ���дӺ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й�һ�Ŷ���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֤���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Ķ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è��ô˵��ͨ�أ��ҷdz�ȷ��ȷ����ֻ��è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Ҳ�dz�ȷ���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Ʊ��Ǵ���һ�߳������ݾ����ҵġ���Ȼǰ�����ҵ�ͷ��ʱ��û�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㹻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˵�è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ѵ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ʨ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ܹ�ѵ���ġ��ܹ�ѵ���ģ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սʤ�ˡ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㹻���ݣ��ص��ĸ����εĵط�ȥ�ˡ�Ҫ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Ͳݴ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 ��ֻ��èһ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Ͳݴԡ��ҵ�ͷѰ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ƻ���û�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ڻ���Ѱ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Լ��ص�һ����ɫ�ĵ��߸˺���ȥ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ճյ���Ϊ��û��Ѱ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ƺ�û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飬Ƥë��ô�ף�һ��ϸϸ�ص��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۵İ�ɫ��Ƥë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ڷ�ӿ��Ũ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䶯��Ƥë�����͵ĹǺۣ����Ǹ��õļ�ʬ���߹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ˮĸ���ҿ�ʼ��ø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š� Ȼ�����ֺ��ɻ���ΪʲôҪ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è�ģ�Ҳû��Ű����è��ɱè���Dz����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ʱ��Թ�һ��è���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̺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ʳè���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¥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룬����ʢ�ź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ɼ�����ϸϸ�ع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ϼ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û�����ݵ�Ե�ʣ������̵ľ�һ��Ҳ�����ɴ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þã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Ķ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IJ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о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̶�ǰһ�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ʱ��Ų����꣬���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ɰ�С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Ը��ȥ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ܶ��ʳ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С�۾����Ĵ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ڴ����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ʲô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ĵĿ�ˮ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Ц�ſ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ҵIJ��ӣ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õġ��⡱�������ҵĿ��С���Ŵ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ʳʱ��ֻ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Dz��صġ���Ϊ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ĵ��ǡ��ó��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糣�ij����ǡ��⡱��Сʱ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Ƿ�Թ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ؼҺ�ĸ�ײŸ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̳Ե���è�⣬����ҳ���è���ˡ� ���룬�ѵ�����Сʱ��Թ�һ��è�ⱻ��ֻ��è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ҳ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ı���ײ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ġ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ȸ����ң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ɱ֮���Һ�Ȼ�е���Ц��һֻè��ȻҪıɱ���أ��ѵ����˻��±�һֻèıɱ����Ȼ��һ���Ҳ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è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Dz�ˬ�ġ��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Ҫ˦������ �ҿ�ʼ�ӿ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Ҳ��ӿ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Զ�ˡ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ͷ��ʱ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ʵ�е��ֻ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ײʱ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Ƥëһ���Ĵ��ۣ�ͬʱ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һ�麮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ȥ�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ŵ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��ں�ɫ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װ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Ĺ�β�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ͷ������ȴ�Ǽ�ϸ��ϸ�ؾ�����è�Ĵ��۵İ�ɫƤë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Եø���ͻ���ͼ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ڹ�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β�Բ���Ҳ���ߣ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ӿ��Դ���Щ��β���ķ�϶�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شӲ�ͷ��̽������ľȻ�ؿ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Ҳ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ľٶ���Ϊ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뼤ŭ��ô��һ���ǵģ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ְ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غ��Ҷ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ң���Ҳ�Ǹ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 ��ʵ����ʹ�Ҹе��߷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εط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һ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һ�ĸ��𡣶������Ŀ�IJ��Ǹ��ӵ�ּ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Ҫȥ֤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ҵķ�ŭ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Ƭ�̣��Ұ��Է��ģ�Ҫ˦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ɵ�ӣ���ķ��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Ƕ�ô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·������ɽ�ȼ��խ���ڵ����ߣ��䳤����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Ӳݣ����վ��п����߳�ȥ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ȴ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ܵŶ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į�ķ��겻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ѲҰܵ���ء��Ҳ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һ��ʬ�������ͻȻ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һ��ɥ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;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ֳ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ⲻ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ܸı�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º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̶����ˣ�ȴҲ��Ϊ��ֻ��è�IJ��Ͻ��棬��Ϊ��˦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è�����ӷ�ŭ�����ҳտ��ܵ�;�У���ÿÿ����ȴ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ֻ��è���۵İ�ɫƤ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İ�ɫ���ߡ���è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ȴʼ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ľ��롣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ʶ��Һ�Ȼ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Ȳ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ң�Ҳ������˦����ȥ���Ҹо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˵�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Զ�ڱ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Զ�Ӳ���ȥ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ˣ���س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Һ�Զ�ˣ�����ֻ��èȴ�վ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İ�ɫ����꣬��ɫ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ˣ�ǰ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գ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о�Ϣ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ͷ�գ��پ��ҵķ�ŭҲ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ζ�ɥʧ���塣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㲻ȥ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㲻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ڡ��ұ㲻�ܹ���һ���𣿿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è�����ˣ��DZ���û���䡣���һֻè�ֲ���ʲô���˵��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ˡ���è�ֲ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۱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η�������߳ܣ���Ϊ��Ϊ��֪�ij��費�dz��衣�������ึ���˱��ܵ�Ŭ������Ȼû��ʤ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㹻�ˡ� ����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ֻ�ῴ��ʤ�������ῴ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ı��ܹ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ʹ�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ϣ��㲻��ʤ���ߣ���ô��Ľ�־ͺ���Щδ�����ܻ���δ��Ŭ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꣬��һ�䲻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ֹ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ȥʧ���ߵ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ܷ�ס��Ц�˵����죬��ʹ���ǿ�غ������⡣Ȼ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ʧ�ܻ��ǻᱻ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 ���һ���̹Ȼ�ص�תͷ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è��ȥ�ˡ���֪���ҽ�Ҫ���ٵ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վ�Ҫ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ʧ�ܵļ�ǿ�����ߣ��ص��ҵij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ڲ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ؿ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ҷ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۵İ�ɫƤë�Լ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۵ĺ����Ŀ�⣬���Ǿ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ǿ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費Ϊ��֪��ʧ�ܲ�Ϊ��֪����Ϊ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Ϊ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պ��˼ɵ��߹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Ҷ����˼ɡ���һ���˺��˼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˼ɵ������ˡ� ��Ϊʲô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ʱӵ�е����ֹ���ĸо��أ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ף���ֻ��è����Ȼ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Ǽ�ŭ���أ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Щ���¡���֪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£�����˶��Ǻ��º�սʤ�Լ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ա����ǣ��Ҿ���֮ǰһ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־�������Ч֮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̵ķ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һ���ؿ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»��к��ˡ���ʱ����Ʋ��dz�·��˳��Ҳ�ɻ��ܽ����ġ���˳��ʧ�ܵ�����ȥ�ɣ��Ҿ�ͻȻ�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Ҳ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 ���ʲôʱ�����ڵ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أ��ҵĺ�ˮ�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ôƴ���أ��ڹ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෴�ķ���Ҳ�ǿ���һ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Ϊ�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 ���һ���ƣ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ܵġ�����ֻ��è��Ȼ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һ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Զȴһֱ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εض����ڵ��ϣ�ƣ�۵Ŀ�����ֻ��è����ˮ�ε��˵��ϣ���į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Ϣ�ţ���֪ƽ�����Һ�Ȼ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�ȷȷʵʵ�Ĵ��ڣ�һ���Һ���ǰ����ֻ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ȴ��֪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·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Ե�����Ҵ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͵ġ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�ô���д�µ�ʱʱ�̵̿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н���֮ǰ��ÿ���˵����˶��ȴ����Լ�ȥд��ȥ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ڸı�����֮˵���ı��ǽ����еĶ����ı䣬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ֺ�̸�ı䣿 ��ʱ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˼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⡣Ϊʲô����Ϊ�ˣ�Ϊʲô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ijһ���ijһ�յ�ijһʱ��ijһ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ͬ�ҳ�Ϊ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è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ã�һ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ֻ��è��ͬ���⡣ ������˫�Ȼλ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̱���ڴ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濴ȥ�����ȫ�ڣ���è���ڡ��谵�ĵ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ϣ��·�һ�ֳ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ɣ�ʲô����ȥ�˼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ܻ߳������𣬶���ȥ��ֻƽ���غ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ͬ����Ƶĵƹ��£���è�ƺ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İ�ɫ�Ĵ��۵�Ƥë��Ŀݻ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Ϸ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롣�ҹ������һ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֪����ֻ��èһֱ�ڿ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ˡ���Ҳ֪����è���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ͬ�飬�ҿ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Ը���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ɻ��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龰�����þ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ɻ��ñ������èִ�ŵĸ��ں��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Ǹ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ֲ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Ժ���Ҿ뵡�����ڴ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ݵ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�ˮ���ε��˶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˰�è�ļ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ź�����ҫ�ɣ��Ҽȸ���ʧ�ܣ��ֺ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ʤ�ߵ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Ұɣ��Ҳ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ܰɣ�����սʤ�Ұɣ�һ�����ɣ��Ҳ����ˣ�һ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һ���Ӱ��һ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 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ǽ�ǿ�����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֩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ѵ���һ֧�̣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ȼ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ĸо�����è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֪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ʤ�����ٹ��ء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˯�ɣ�ֻ��˯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ߡ��Ҳ��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о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צ�Ӱ�ץ���ҵ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ʱֻ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˯�ţ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ˡ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ü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ÿ���ø�����ʱһ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ɪ���ı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İ�è�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ݹ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Ƥë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Ƥ���ϡ� ���ҿ����İ�è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ҡ� ��è�������õı�������ز����Ӥ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ȥ����Ϊ�һ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 �Ҷ�Ȼ�е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뷨�Ƕ�ô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һֻè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е��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ѹ�Ȱ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ĺ�Թ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˵�����յĻ��ơ���ֻĬĬ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ͷ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˺þã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̧ͷ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Ӱ�ˡ� �Ҹе�ʮ�ֱ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ɻ��ñ���ҸϽ�̤����ȥ��ȡ��ɻ��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ķ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--��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ñ�ӣ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û�е�ͷ��û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죬�ܿ����ı�Ӱ��ģ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Ҳ�֪���룬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õ�ɻ��ñ���Ҵ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ܾ��ˣ�����֪Ҫ��ʲô��
����: 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 ;ԭ����: Īͩ ΰҲ��
|